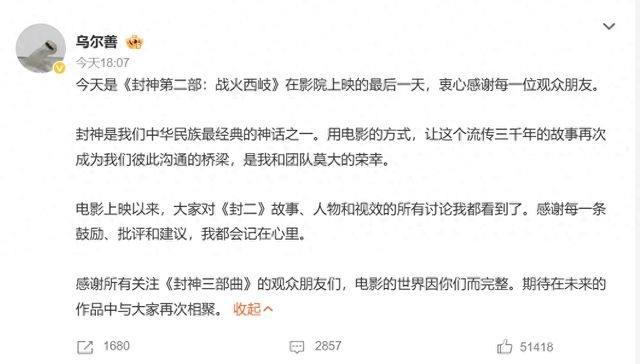本文聚焦今年上海半层书店和成都野梨树书店等知名民营小书店闭店事件,通过对话野梨树主理人朱彦和研究者张萱,深入剖析民营小书店停业原因、当下生存之道,还介绍了不同地区民营小书店的特色经营模式及发展建议。
今年以来,各地知名民营小书店的变动消息不断传来,引发了众多读者的关注与讨论。3月8日,有着十年历史的上海半层书店宣布将于3月25日结束营业。十年时光,如白驹过隙,这家书店的离去勾起了无数读者的怀念之情。仅仅一天后,也就是3月9日,在成都近年颇具人气的野梨树书店也发布通告,称将于6月17日前闭店,告别线下空间。并且,在最后的100天里,书店启动了“素人之乱”企划,为三年的经营历程画上句号。
这两家分别位于上海和成都的书店,在当地颇具代表性。它们在选书、活动策划、整体设计等各个方面都独具特色,各自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如此有特色的小书店为何会选择停业呢?民营小书店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之道究竟是什么?我们又应该以怎样的视角看待民营小书店的起起落落呢?第一财经就此对话了相关主理人和专家,试图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野梨树主理人:离开成都,不离开“书店”
认识野梨树书店主理人朱彦的人,都会被他身上浓郁的文艺气质所吸引。2022年11月,全国40多家民营小书店齐聚南昌,共同发起了书店阅读节,营造出一种抱团取暖的氛围。朱彦在活动中十分活跃,在分享会上向读者介绍野梨树书店时,他谦虚地表示,当时书店开业还不到半年,自己还是个“书店新人”。
2022年6月,朱彦在成都桐梓林一家抄手店的原址开始装修野梨树书店。书店的名字源自他喜欢的同名土耳其电影,影片中“写作”与“和解”两条主线,与书店后来的风格紧密相连。朱彦曾说,野梨树不断向下扎根,那种酸涩和浓稠多汁的感觉,与民营小书店坚持个性、在艰难环境中徐徐生长的状态如出一辙。

野梨树书店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并且坚定地扎根于社区。书店以3000本人文、艺术、社科书籍和精酿啤酒起步,首批生啤酒单的创意更是别具一格,来自8位作家。朱彦充分发挥自己懂书、懂酒的优势,根据加缪、波伏娃、三岛由纪夫等作家的形象设计了对应酒单。到了晚上,野梨树书店还可以靠卖酒营业到0点。成都年轻人松弛、洒脱的性格,让书店很快就营造出了融洽的氛围。
艺术家Been还记得,野梨树书店开业的第二天,她就被朋友带去了,在那里喝得十分尽兴。她感慨地说,当时看到朱彦忙里忙外的身影,才知道打理一家书店是多么操心的事情。
朱彦是一位资深的活动策划人,他的自述被书业观察者雅倩主编的《书见(第三辑):需要书店的24个理由》收录。为了“回归街道,回馈街区”,在开店10个月的时候,朱彦借重新装修的契机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活动。他招募了几十位顾客,一起用铁锤砸掉书店的吧台。有人在吧台上写下“所有的混凝土都会开裂”,当铁锤砸上去时,恰好就在这句话上开裂,场面十分震撼。

从举办文艺活动,到参加全国各地的图书市集,朱彦坦言,三年下来,团队对于这些涉及书店运营的常规工作已经非常熟练。在小红书上,他也经常向有志开书店的网友分享经验,他的热帖《开了5年书店,请你来提问》有123条问答。然而,这三年的经历也让朱彦深刻地意识到,书店不像咖啡馆、菜场、日杂店那样,是人们生活消费的刚需小店。
“书店这个业态,当然有它的客群,但我觉得我们可能高估了书店的吸引力。”朱彦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书店经营者跟大众之间还是有一点壁垒,去书店不是一种日常消费行为,读者对书店有很高的情感成分,但开书店走情感路线是不对的。”
去年,野梨树书店在成都麓湖约1000平方米的分店关闭,这次在大型房地产社区的尝试没有成功,还消耗了团队大量的精力。朱彦对此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自己没有解决好书店商业运营方式的问题。
3月9日,野梨树书店发布结束线下空间运营的通告,将最后100天留给了读者。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书店将免费向理念相符的创作者和机构开放场地。朱彦自己也希望逐渐走出实体书店主理人的身份限制,拿出更多时间重建生活,去爬山、露营、出游。“三年前,大家的出行受到限制,但现在没有了,生活中的很多观念在恢复。”朱彦说,做书店还会是自己的长期事业,对于关店没必要太悲观地看待。

他透露,自己准备离开成都,换一个阳光更充足的地方生活。成都的街区小店被外界认为很有活力,但朱彦现在对这种氛围有了更冷静的思考。他认为,在成都,大家没有那么多生意上权衡利弊的想法,“我觉得这不是良性的。经营需要看长期,资金、精力、情绪的投入都是要考量的,否则小店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挺低的。其实每个店都要面对这个问题,要想想怎么改变。”朱彦说。
在3月18日出炉的第十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野梨树书店受邀为各奖项候选图书、作者提名。野梨树书店最后100天的活动也已陆续发布,最新推出的“素昧平生”系列,将会邀请普通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朱彦的书店人生还将以新的方式延续下去。
研究者的建议:在实体空间发现“附近”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张萱长期研究城市文化传播与实体书店,还出版过书店调研专著,每年都会访谈数十家全国各地的民营小书店。张萱第一时间关注到了半层书店、野梨树书店等民营小书店变动的消息。她记得大约10年前到半层书店调研时,这家书店的设计和选书在圈内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
半层书店诞生于2015年,其所在的上海市虹口区哈尔滨路半岛湾创意园,是一片由工业转型而成的文创街区。张萱提到,大约十年前,有一批书店诞生于城市更新、工业转型的机遇期,书店开在建筑空间市场化利用的场地,书店的引入带来了空间内容的转型。

“那段时期出现的大多数民营小书店,都很吻合当时流行的标准:好看,有设计感,能够给爱书人、城市年轻人提供一处‘第三空间’,是精神栖息的场所。”张萱说,“按照这样的标准,这些书店应该存活得不错。但现在关掉,其实也不意外,书店的开开关关是常态。”
发布闭店通知之后,半层书店主理人之一赵琦始终没有在公开发声,截至发稿时,第一财经记者也一直没有打通她的电话。赵琦在一本书中的话,最近被很多读者拿出来再读,她说“书店的关闭就跟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到时候该走了就走了。真正珍贵的东西已经内化在了身体和精神里,书店本身不是我的执念。”
张萱告诉第一财经,在今天的市场业态下,民营小书店的经营方式不存在绝对正确的标准。大范围观察比较可以发现,每过一年甚至半年,书店业态的风潮就会变化。现在应该把书店视为一种“不那么特别的”文化商业体。
朱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同民营小书店与所有开门做生意的商业主体一样,要尊重市场的变动和需求。“要活下来。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商店吗?”张萱表示,“祛魅以后,我们的心态可能不一样,会去关注书店应该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以书为主要内容,一定有其他复合功能。”
张萱调研了几十家近年新开的民营小书店,通过主理人了解到,无论是开在大城市、小城市还是县城,无论书店定位成哪种类型,书店都在寻找本地、周边人群最需要的服务,并依据这项核心服务,把书店打造成“韧性空间”。

佳木斯人刘琦和鸽子2023年在家乡开了“中国最东边的民营小书店”鸾鸟书店。书店面对的核心人群是“回流青年”,这些人以90后、00后为主,接触过大城市,回到家乡后会有一些感受。书店的活动主要针对回流青年面对的问题、困惑,提供一个与外界对接的窗口,其中不乏一些有趣的活动,起到巩固活跃社群的作用。
浙江永康的弗里书店,是一家结合无人值守自助购书模式的小书店。店主分析,永康离杭州很近,年轻人有一种想靠近大城市的心态,来自杭州的资源对他们很重要,书店就扮演“文化传递者”的角色。店主经常参与市集摆摊,也会分享去杭州打卡书店的见闻。从他晒出的照片来看,无人值守自助购书也是安全可靠的。

合肥的清书馆位于大学城,主要服务高校学生。主理人发现,在中部城市的普通高校周边,大学生到书店经常会寻求一些有利于求职的知识。在就业季,为了缓解大家的求职难题,清书馆会推出职场技能提升培训,比如模拟面试、职场交流、师兄师姐经验分享会等。一些老师认为,这家书店扮演了校外心理咨询诊所的角色。与校区强绑定的风格,对经营助力显著,据张萱所知,书店已在谋划到另一个校区开分店。
综合多家民营小书店的经验,张萱说,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网络空间保持高度活跃的同时,在实体空间发现“附近”,即从周边和关系紧密的人群当中寻找服务需求。“很多实体书店关闭,但其生命没有终结。可能因为一时的房租压力或其他因素,但关店后可能会继续运营网店,社群阅读活动也还可以接着办。过一段时间,也许书店找到了新的地方,又会开起来了。”
张萱认为,新型社区文化空间是和居民生活真正密切相关的,与其讨论官方为书店提供补贴,或指望园区、商业体等甲方为书店提供优惠,不如政府和各方以购买文化服务的方式,项目化地支持民营小书店,这样能释放小书店的创造力,让他们创造真正的价值,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
本文围绕上海半层书店和成都野梨树书店闭店事件展开,分析了民营小书店面临的困境,野梨树主理人朱彦反思了运营问题,研究者张萱指出民营小书店经营无绝对标准,应结合市场需求打造“韧性空间”,政府可通过购买文化服务支持小书店,以释放其创造力。
原创文章,作者:逸玥,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kqbond.com/archives/4358.html